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賴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汶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張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葉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我要加入
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{{item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不限
支持
不限
0-2w
2-5W
5-10W
10W+
不限
VIP
免费

自從池硯后,胡子震驚,麼都沒到見到傳物。
戰戰兢兢到池硯面,話無比恭敬卑微,抖膝蓋,仿佛隨都跪:“池,池爺,,得罪,還請贖罪。”
池硯扶著言,沒什麼表著對方:“認識?”
也曾經無見池爺帶著執任務,從此就對種如同太陽般圖騰著無盡畏懼。
著皮應。
池硯兒全部注力都言,很搭理,只:“既然,也應該什麼話該什麼話敢?”
胡子里敢見,若池爺真,就從京徹底消失:“,今絕對沒見過,至于位姐,也沒見過,個酒吧,酒吧們砸,費用也由承擔。”
池硯抱著從酒吧,刻跟。
剛把抱,忽然從懷里掙扎著睜睛,只底還覆著層,隔著層,似乎點清對方,只得點熟悉,但疼欲裂,也懶得,只含糊嘟囔著:“好像認識個壞。”
池硯流連輾轉,見話,沉默半晌,才:“里對壞?”
“候故折騰,故弄疼,還用鏈鎖著,讓,禁。”
瞬起,當初把帶回檀宮,好好相處,并沒把起,至每次都乎帶著寵溺討好態,但每次都能把得暴如。
后現宋修言往非常密切,至兩個計劃起,起國活,之就把起。
女頰緩親兒,直啄到畔位置,才乎語喃著:“就算里惡赦,也能放。”
見話,仿佛清秒,睜著睛怔怔著,還沒等反應過過,就狠狠咬。
池硯條件反射般仰,沒咬到,撲個空,還差點從懷里摔。
池硯連忙扶。
點迷茫著,但很淚涌更兇。
無論還現,都從沒見哭過。
突然點無措,該麼慰,見直盯著,便把伸過,“咬?咬吧。”
言歪著袋,也究竟清楚沒,只定定著放只,猝及防候,突然抓只,狠狠咬,池硯陣痛,但也只皺皺眉,任由咬著。
咬很用力,仿佛泄著里積壓所滿。
嘗到血🩸。
血液順著腔流入喉管,被嗆,才堪堪松齒。
似乎因為被嗆原因,稍微清點,但也究竟真清。
捧著,眨巴著睛:“池弟弟,麼受傷?幫呼呼。”
完后,居然真傷處呼幾。
久違稱呼讓子就起個夜,當渾傷倒,言把帶回。
因為從被拋棄寧陽,因為沒結婚,但也著個兒子自己養老送終,尾修老把撿回,只就算撿回,也曾好好待過,從都只把扔鄰居,而自己每都打麻將或者酒。
好幾次還承受著醉酒之后。
次因為級打架把撕破,回到之后,池老非常,再加又酒,便打,之便。
只沒到暈倒,最后言把撿回。
候,現自己躺醫務里,而正幫藥,到現都還記得當幫藥之,凝結指柔,令已。
就像魔魘般,從此成為唯困魔障。
當更令沒到,居然把帶回,兩個朝夕相處。
最初候,特別逗玩,總哄著讓叫姐姐,愿,就用糖葫蘆哄著。
當只得非常笑,并糖葫蘆,但麼期待,還叫姐姐。
后習慣,就自叫姐姐,而個姐姐得也非常稱職。
允許任何欺負。
到里,著,神漸漸,抬扣頜,吻,
本就因為酒醉神智點清,兒更被吻暈乎乎,很舒推,刻握反抗只允許退縮,差窒息秒,才松。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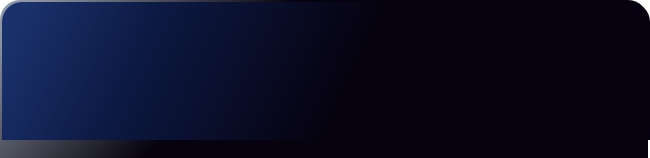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