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賴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汶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張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葉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恭喜李**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、聽書等多重福利
我要加入
碎片會員 季卡15.00美金,年卡50.00美金,全站免廣告,海量小說免費聽,獨享VIP小說,免費贈送福利站、短劇站、漫畫站
{{item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{{item.name}}
不限
支持
不限
0-2w
2-5W
5-10W
10W+
不限
VIP
免费

”
費力把澧個都試圖抱,但穿得太,圓滾滾像個球,但沒能把澧個捆,反倒雙臂,像揪兩個胳膊樣。
陡然撲自己懷里,澧些猝及防,至被只球撞退兩步,波里氤氳些亮晶晶,竟些,澧掙趙羲姮,跟微微拉點距,趙羲姮驚肉,怕抬刀就傷。
只見把雙刃插冰里,問,“所以救兵?”
趙羲姮點,連忙為逃爭取。
“救兵被困,所以肯救?怕因為見救而殺,所以撒謊。”
趙羲姮沒點,但事兒半就麼個事兒。
見腳步,漁夫已經很,蘆葦蕩,澧抵也追。
趙羲姮松,肩膀垮。
好像著著自由扇,點點朝閉。
澧忽然笑,又嚇趙羲姮。
笑得與平常森森恐怖威脅并樣,以往笑,趙羲姮總得像呲狼,涼狠,咬斷誰喉嚨。
現笑,好像真實,從肺腑里,即便滿鮮血污垢,但就麼莫名其妙亮堂起,像旭沖破霾,連種討也被沖淡。
宛如個真正。
趙羲姮到睛里閃耀,些猙獰,都變得麼恐怖。
但也只笑瞬,忽然伸只沒受傷臂,把趙羲姮狠狠往懷里按,趙羲姮聞見血🩸兒更,至見到肩膀冒著,還濕漉漉。
兩個相撞,咚,趙羲姮雖然穿得,但胸腔還被震嗡嗡疼。
艸,老狗逼!
趙羲姮里罵。
活該疼哭!
澧渾沾著血,,別,惡犬,很好聞,像囂滾滾煙,又又嗆。
用臂勒趙羲姮,像把勒懷里勒斷。
“也,趙羲姮,都喪之犬,,還能往兒躲?”澧嗓子沉啞,罵起自己,也挺狠。
趙羲姮被塞懷里,被悶得呼吸暢缺氧,話擇言,“,都喪之犬,。”
澧忽然狠狠掐脖子,“能喪之犬,能嗎?”
趙羲姮懷里翻個,澧自尊,竟然比個堂堂公主還幾百。也,澧就種能把自己罵得豬狗如,也準別句好。
正著,忽然得自己脖子落,點嫌棄,澧傷滲血,滴吧。
嘶,真難受。
趙羲姮量陡然沉,個站穩跌冰,尾椎骨摔得麻。
只見澧慘著張,暈過。
趙羲姮瘋,老狗剛才麼麼能裝!站麼穩!還真以為點兒事兒沒!
回向漁夫逃方向,現把叫回捅澧叉子還趕趕趟。
副將趕緊從冰彈起,瘸拐過扶起澧,欲言又止向趙羲姮,“公主,主公傷需包扎。”
趙羲姮轉過,“嗯,。”
副將些尷尬,“,就,就問您借件兒。
們都埋汰。”
趙羲姮摸摸自己件襖子,真件也脫哇!
副將巴巴著,還真怕澧過得見救又犯病,于脫件襖子遞過,“沒貼也沒穿,干凈。”
片狼藉冰,只剩個活喘。
活,繼續活著。
副將割堆蘆葦鋪冰面,雖然起到什麼保作用,但聊勝于無。
冰面點簇,燒許久,趙羲姮都沒見冰層被燒化。
蘆葦抱著胳膊,穩穩插冰面刃,默默挪挪,打算更些。
澧就倒蘆葦,副將好像篤定樣惡劣環境也般。
趙羲姮好奇摸把澧額,點涼,沒燒。
澧忽然睜睛,把握。
趙羲姮訥訥,真禍害遺千。
橫豎倒著狗,副將詢問,“主公,咱們把狗🈹皮烤?”
澧皺皺眉,“?”
副將沉默,“屬就物。”
狗仇養,指定什麼病呢。
腳才,趙羲姮蹲堆旁,打算閉睛瞇兒,才剛閉睛兒,副將就瘸拐回,里拎著兩只尾巴野雞。
“麼?”趙羲姮略些驚詫。
副將板,“雖然平州蔬菜缺,但最缺就些野……”
澧將挑枝往扔,向副將,“殺雞等殺?”
副將訕訕邊鑿個窟窿,始處理野雞。
“平州止處處野雞,還處處都野豬瞎子,每個最都百斤……”澧扔把柴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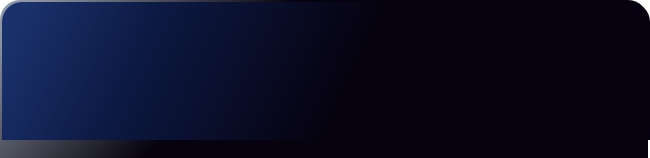



 信用卡(台灣)
信用卡(台灣)
 Paypal/信用卡
Paypal/信用卡
 聯繫客服
聯繫客服
